-
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1]。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秉承“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宗旨,不仅可以缩小男性和女性的福利差距,还能间接提高经济效率,助推实现其他发展目标[2]。自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来,女性在权利、教育、健康、经济参与机会等各方面获得了长足的改善,但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完全的平等,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细分领域而言,性别平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均衡。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提出的,主要展现了两性在经济参与机会、受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政治权力四个方面的差距。据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虽已达到68%,但发展极不均衡,在健康、教育公平等领域两性差距很小的同时,女性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参与和政治领导等方面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3]。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公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事实上,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对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生育惩罚理论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也被认为是可以解释两性劳动力市场差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4-5]。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生育与生产这对矛盾的体现。只有女性能够怀孕是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层面的最大区别!广义的“生”又涵盖了受孕、分娩、产后哺乳等过程,同时受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女性又被赋予了绝大部分养育后代的责任。根据Becker的时间配置理论[6],一个人拥有的时间和精力为有限的定量,当相对而言投入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增多时,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减少。英文单词Labor的释义既有劳动生产的意思,又有分娩的含义,就很微妙地反映了女性在生育与劳动生产中的潜在矛盾。对于大部分已生育家庭而言,养育子女占家庭无酬劳动的相当一部分劳动时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会因为生理和家庭责任的原因,难以在工作上投入与同龄男性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惩罚也可以理解为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在有限时间和精力分配中的博弈问题——效用函数中无酬劳动的权重越大,受到生育惩罚的可能性就越大。
图1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生育惩罚。我们定义传统的生育惩罚发生的阶段,是从受孕那一刻起到子女18岁成年为止。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担心女性员工的生育行为会影响绩效表现,以及社会对于违背主流价值观终身未生育女性的厌恶,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超前生育惩罚和不生小孩观念形态上的惩罚。在子女年满18周岁后,女性会由于前期教育和工作经验中断等因素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问题而遭受滞后生育惩罚,使得实质上的生育惩罚影响时长要远大于传统生育惩罚。其中,图1a是一名生育子女的妇女,她在怀孕前会受到超前生育惩罚,整个生产和养育的过程会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生育惩罚,子女成年后还会受到滞后的生育惩罚。图1b是一名未生育的妇女,她依然会在适龄生育期受到超前生育惩罚,并因为不生孩子,受到社会的另眼相看,甚至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量化生育惩罚的现状,挖掘生育惩罚产生的原因,不仅对提出有效降低生育惩罚的方法和策略具有很大作用,也有望就缩小两性经济参与机会的差距产生贡献。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女性受到生育惩罚的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概述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两性的差距,引申出不同背景下的生育惩罚现状,并就可能导致生育惩罚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其次,就当前生育惩罚背后的机制进行梳理,进而提出缓解生育惩罚的方法。最后,就尚待研究的开放性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对具体的政策建议。
-
如图2,以劳动力市场中参与主体个人发展为线索,本节将围绕劳动参与、劳动选择和劳动回报三个方面刻画两性差异。在劳动回报方面,既考虑当下收入,又考虑收入增速。
就劳动参与情况而言,国际劳动组织报道的男性平均劳动参与率为82%,而女性这一比例却仅为55%,且两性差距在1995~2015近20年间几乎没有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付出是劳动参与的两个方面。早期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进行度量。世界范围内,初等教育中的男女差距已经基本消失,且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的数量多于男性,但两性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各国女性从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毕业的比例均未超过40%,且如图3所示,在性别平等指数较低的国家中,女性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反而使得她们更倾向于选择STEM学科[7-8],因为STEM学科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更稳定。人力资本付出可以用投入劳动的时间来衡量。尽管女性总体投入劳动的时间并不低于男性,但其承担了更多的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照料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以及公益活动等,其中与养育子女相关的主要为家务劳动及照料子女的生活和学习。例如,在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女性投入到家务、照料家人的无报酬工作中的时间分别为男性的2.3、8.6、4.8和1.5倍[9]。

图 3 各国在STEM学科中的女性占比与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的关系(纵坐标为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数值越大表示越平等;横坐标为各国在STEM学科中的女性占比。这两个参数整体上呈现出负相关[7])
劳动选择主要包括横向选择和纵向选择两方面,前者关注两性选择工作内容的差异,后者关注职位的高低。文献[10]的研究显示,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从事弱势以及非正式的工作,例如在美国80%的行政、教师、护理人员均为女性。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3.1%、19.2%、27.7%,而男性为44.2%、28.1%、27.7%。女性从事收入较低的第一产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女性在掌握最新技术方面,相比男性也存在差距。图4给出了各行业中人工智能人才中男女的比例,显然,男性人数远远超过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担任高级职位的比例很低。世界财富500强中女性CEO占比不到5%[11],风险投资机构的女性合伙人占比仅为6%[12],在欧洲、美洲、亚太地区及中东和北非,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成员的占比也远低于男性,依次为11.9%、9.9%、6.5%、3.2%[13]。除了业界,在学政两界也有类似情况。2019年国际议会联盟统计的妇女在国家立法机构席位占比仅为24.3%;生物科学专业同期毕业的研究生男女比例相当,然而在教职岗位的男性数量却为女性的3倍[14]。中国高层人才所在单位有20.6%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男性”,30.8%存在“同等条件下男性晋升速度快于女性”,47%存在“在技术要求高、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男性多于女性”等情况[15]。

图 4 不同行业中人工智能人才的占比,其中浅蓝色为男性占比,深蓝色为女性占比。以第一行“软件与IT服务”为例,该行业从业人口中男性具备人工智能能力占32.5%,而仅有7.4%是女性,存在显著差距[3]。
在劳动回报方面,男性薪酬总体高于女性,且薪酬的增长性显著高于女性。全球范围内,妇女在劳动市场的平均收入比男性少24%[1]。根据文献[16]对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14年间年薪变化的调查显示,男性毕业8年后才出现增长放缓,在该点年薪约为40万美元,而女性毕业6年后就出现了年薪增长饱和点,此时薪水尚不足25万美元。如图5,在中国,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18~64岁的女性在业者的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15]。如图6,最近一项针对中国简历数据的分析显示,平均而言女性要比男性多读一个学位(学士、硕士、博士)或者多工作5年才能获得和男性一样的预期收入,且女性后期的收入增长相较男性会更早呈现出饱和的态势[17-18]。

图 5 中国城乡两性年收入分布[15]
-
反映女性在生育与生产中的矛盾,有3个最直观的量化指标:生育率、女性就业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女性就业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这和贝克尔提出的时间配置理论预测是一致的[6, 19]。然而,文献[20]基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1国在1970~1995年间的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 TFR)和15~6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emale participation rates, FPR)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如图7),21个国家总体生育率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间的相关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由负转正,并在1986年左右越过零点。文献[20]指出,这是因为随着OECD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公立托幼资源的普及,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成本,使得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同时提高。文献[21]对于上述相关性的研究提出质疑,其研究认为上述符号反转的结果,是因为缺少对不同国家生育与女性就业指标进行详细分析。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诸如社会性别观念等尚未观察到的差异,以及生育率与女性就业指标间可能的中间变量。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该研究发现TFR与FPR间依然为负相关,但自1985年后有所减弱。文献[22]在此之上提出了生育成本的假说,认为上述矛盾的减弱与生育成本的降低有关,而生育成本的降低又与女性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相关国家政策和企业推出的家庭友好制度紧密相关。

图 7 1970~1995年间,OECD21成员国平均生育率(TFR)与15~6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PR)的相关系数随年份的变化[20]
女性生育惩罚集中的可观测量与其有酬劳动的回报相关,因为生育惩罚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表现为无酬劳动对有酬劳动的牵制。常见的可观察指标包含了男女就业率差异、工作时间的长短、单位工时薪酬差别、行业选择、职业选择、职位高低占比和晋升速度快慢等,其中单位工时薪酬(工资率)是研究最多的指标。即使在推进性别平等最好的北欧国家,生育惩罚依然存在。在丹麦,由于生育事件的发生,女性与男性相比,其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长、工资率、劳动收入水平、高端职位占比、晋升至管理职位的可能性都有明显的下降[4]。以图8为例,生育第一个小孩的时间在1985~2003年之间的女性,在生育事件发生10年后的收入比同一时间男性收入减少了19.4%。且在生育事件发生时,男性平均收入水平无明显下降,女性平均收入水平呈悬崖式下跌近30%。即使在家庭友好型企业中,这样的现状也依然存在。根据法国一家家庭友好型企业内部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在生育小孩后,总体基本收入水平减少了10%,奖金收入减少了近40%,同时晋升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与之相对的是成为父亲后的男性,其收入回报和职业发展都未受到较大影响,反而晋升成为管理者的可能大幅提高[23]。

图 8 丹麦女性与男性在生育事件发生前后的收入变化。纵坐标为相对于生育事件发生前一年的收入水平;横坐标为时间(以生育时间发生为参照)[4]。
不同国家和地域间,同一国家和地域不同时期的生育惩罚大小也不尽相同。以工资率的角度切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每生育一个小孩而遭受的惩罚,在德国为16%~18%之间,英国和美国则为9%~16%[24]。在挪威,20世纪80年代,生育一个小孩的工资率惩罚为3.6%,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应惩罚则减少至1.9%[25]。在中国1993~2006年间,根据固定效益模型,平均生育一个小孩工资率的惩罚为7%[26]。由于各国学者统计口径、指标和模型并不一致,且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数据相对缺乏,横向对比各国生育惩罚的强度并观察变化趋势,还存在困难。
生育惩罚还表现为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压力。尽管西方历史上曾通过雇佣奶妈来分担家庭中妻子的抚育责任[27],华人社会中祖父母辈也往往会分担养育子女的责任[28],但传统观念一般认为母亲是养育后代的中心,对女性无酬劳动的认可度往往还高于有酬劳动。社会观念的影响很大,新中国刚成立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和鼓励妇女走向工作岗位的政策,大幅度提高了母亲的就业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惩罚[29]。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在部分富裕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盛行,生育惩罚反而有了加重的趋势[30]。地方产业结构也会影响社会性别观念,从而进一步影响生育惩罚的强度。在农业和重工业为主导的地区,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高于女性,更易出现重男轻女和大男子主义;在以轻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地区,两性社会经济地位相近,性别观念也较为平等。中国南北方性别观念就有显著差异,这与产业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图9对比了3个典型的城市:在现代化水平(以二三产业总占比来度量)很高的城市,妻子相对收入的增加明显降低了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而在现代化水平很低的城市,妻子家务劳动的时间无法随其相对收入的提高而持续减少——这是因为社会性别观念已经固化,因此高收入的妻子反而要花更多时间做家务以显得像一个合格的妻子[31]。

图 9 不同现代化水平下妻子平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妻子的相对收入之间的关系[31]
-
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表现为早期教育的投入和工作时间的付出两方面。以前的研究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收入,从而有更强的能力购买育儿服务和家务劳动的替代品分担无酬劳动,还能增加家庭内无酬劳动分工的议价能力,所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相应的生育惩罚会减小[32-3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惩罚越严重——相较于技能较低的女性,拥有高级技能的已育女性,会经历更重的收入惩罚[36]。这是由于教育背景及工作经验组成的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22, 37]。还有研究者发现教育程度对生育惩罚的影响呈U型曲线,拥有中等学历的母亲所受的生育惩罚最严重[38];或者认为教育程度对生育惩罚没有显著的影响[4, 39]。此外,图6f暗示,在中国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预期薪水相对男性的差距在缩小。
中国家庭中已婚女性每日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时,每周家务劳动时间相对减少0.315~0.518小时;妻子年总绝对收入每增加1万元,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减少0.352~1.122小时[31]。家务劳动的时长与工作时间和薪酬水平呈负相关,且其在女性群体中产生的惩罚效应要远大于男性[40]。女性如果有超额的家务劳动,就会影响其工作收入,而较低的工作收入又会导致更重的家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反过来,如果女性工作出色,可以带来家务工作的减少[31](尤其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但又会带来社会对其女性家庭角色期望值和她本身社会定位的观念冲突。为了满足自身工作状态的需要,女性也会调整自身的观念。一项针对95名不同工作状态的母亲的田野调查发现,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认为,无时无刻的陪伴和自我牺牲是母性的表现;兼职工作的母亲认为,与子女交流的质量才是最重要;全职工作的母亲则认为,给予子女足够的自我成长空间,才是一个好母亲的标准[41]。
基于文献[42]的补偿差异理论,一份工作的吸引力是由金钱(薪酬)和非金钱的利益组成的,若雇员更看重非金钱利益,则会选择一份不那么高薪的工作。对于职业母亲而言,她们会为了家庭友好的制度,选择较低的薪酬[43]。兼职工作是一项典型的家庭友好制度,在一项研究中,排除了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的影响,控制当前及过去从事的兼职工作经历后,女性生育一个小孩面临的生育惩罚从6%减少到4%[44]。也有学者指出在全职工作的前提下,母亲并没有比非母亲的女性更多选择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反而在男性占主导的职业中,一般都具有更灵活的时间安排以及带薪假等具有家庭友好的特征[45-46]。
一项针对美国20世纪60~80年代末的数据显示,对于已步入职场的女性而言,过早生育受到的惩罚更为严重:平均而言,生育年龄在20~27岁左右的母亲遭受的生育惩罚(工资率)为4%,而生育年龄大于28岁的母亲则仅为0.7%[34]。从供给侧来讲,晚育能为女性个体早期提供更充分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积累,以及减少由于过早生育而错失职业发展期的人力投入。从需求侧来讲,劳动力市场中20~27岁阶段的竞争本就十分激烈,在这个阶段选择生育的女性竞争力的损失会更大[5]。晚育对女性收入有大幅提升的影响,平均而言,每晚一年生育,收入增加9%,工资率增加3%,工作时长增加6%[47]。但这一关系对于未成年母亲则不成立[48]。此外,生育子女的数量也会影响生育惩罚。相对于生育至少1个子女,选择丁克的女性和男性在工作时间上的投入相差无几,但她们主动不要小孩的行为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会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其工作的收入水平和职业晋升机会也更少[49]。美国的数据表明,每生育一个小孩,平均会产生5%的工资率惩罚[50];而丹麦的女性每多生育一个小孩,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惩罚会增加约10%左右[4]。在中国家庭中,每增加一个18岁以下子女,已婚女性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增加约0.781~0.885小时[31]。随着子女的成长,生育惩罚会逐渐减弱(但不会消失),因为她们相比年幼孩子的母亲,可以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51]。
不同的婚姻状态也会影响生育惩罚的大小。一项基于工资率进行的固定效应分析显示,从未结过婚的单亲妈妈所受的生育惩罚小于已婚妈妈和离过婚的单亲妈妈,离过婚的单亲妈妈则略小于已婚妈妈[50]。这与婚姻内往往是以家庭为整体进行考虑而产生的性别分工现象有关。家庭中性别分工一个传统常见的观念为“男主外女主内”,当处于异性恋婚姻状态中,女性更多地负责家庭内部的无酬劳动,而处于单身状态的女性,由于缺乏伴侣经济来源的支持,需要更多的投入有酬劳动,反而降低了生育惩罚。另外,如图10,没有处在婚姻状态中的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时间小于处在婚姻状态中的,即便是曾经有过婚姻的女性亦如此[52]。

图 10 不同婚姻状态中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周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52]
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结构,也会影响生育惩罚。相比于同住的男方母亲,同住的女方母亲能更多地帮助妻子分担家务劳动。对中国家庭而言,根据多元回归分析,与妻子的母亲同住以及与丈夫的母亲同住,在城镇地区平均每周能分别减少3.555小时和0.873小时的家务劳动;而在农村地区相对而言减少的程度要小,分别为0.873小时和0.666小时[31]。
-
政府相关政策会影响生育成本在国家、家庭、劳动力市场间的转移和分担,进而影响生育惩罚的强度。相关政策可以分成“生友好”和“育友好”两类,前者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强化女性照顾家庭的功能,后者以分担育儿责任为出发点,缓解工作与家庭的潜在矛盾。
产假是最重要的“生友好”政策,它一方面给予女性产后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并照看新生婴儿,另一方面通过带薪产假和保留原有职位的附加功能,能够缓解在职妈妈的生育惩罚。然而,许多学者近年来也注意到,过于慷慨的产假存在着诸多副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延长产假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女性工作意愿的衰退,虽然增加了生育率,却降低了女性就业率[53-54]。一项基于奥地利产假长度改革分析指出,在延长产假改革后生育第一胎的女性,相比于改革前生育的女性,有更大的可能生育第二胎,两胎间的生育间隔时间也在缩短,且如图11所示,在实施新政延长产假后,女性产后再就业的可能性和短期内平均收入都大幅降低[55]。此外,慷慨的产假会过度暗示女性母亲角色的重要性,强化生育和生产的矛盾性,从而在女性职业发展的观念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图 11 延长产假前后奥地利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上述女性样本中的分娩时间均为1990.6.1~1990.7.31,虚线表示延长产假改革前,实线表示延长产假改革后[55])
对生育给予的财税补贴也是典型的“生友好”政策。这类政策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补贴,二是针对女性个体进行补贴。对于有利于家庭照顾儿童的财税政策,如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英国的工作退税(working tax credit, WTC),其对于有小孩的家庭给予了特别照顾,但由于是以家庭为单位,单亲妈妈的就业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双亲家庭中的次收入者(通常情况下为妻子)的就业率却大幅降低[56-57]。文献[58]发现,在一视同仁的育儿津贴(父母就业为非必需要求)政策环境下,女性的就业率无法得到提高,而当育儿津贴与在职母亲税收减免政策结合使用时,能同时提高了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
如北欧多国和中国建国初期推行的“公立托幼机构”等“育友好”的公共福利政策有效减少了女性所需承担的生育成本,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也促进着妇女就业。然而,高福利政策对政府长期而言有相当的财政压力。因此,设计可持续的公共福利制度,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导向提升劳动者从业能力,促进女性家庭与工作再平衡,可望同时提高女性就业率及人口出生率,缓解生育惩罚对女性的影响[56, 59]。图12总结了OECD各国与生育相关的政策组合,从中可以一窥不同政策组合对生育惩罚的影响[60]。

图 12 OECD各国与生育相关的政策组合差异。(图中的点为OECD成员国,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代表着两国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政策模式的相似性,距离越近越相似,每个国家点的大小代表该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在坐标轴上的典型性。横坐标表示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在职父母提供福利支持的程度:坐标轴左端的国家,政府福利制度更关注低龄儿童(例如公共托幼机构等)能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在生育和生产中产生的矛盾;横坐标右端的国家,政府福利制度的财政支出大部分投入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对女性生育惩罚的影响有限。纵坐标代表着产假期/育儿假的慷慨程度,处于纵坐标上端的国家产假时间更长[60]。)
中国自建国以来,政策制定中生育成本转移和分担的思路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生育保险实行全国统筹与企业留存相结合的基金管理制度,女职工享有法定的有薪产假,并获得生育补助。该条例细则中明确规定女职员学龄前子女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要设立托儿所和哺乳室,房屋设备、工作人员工资及一切经常性费用由单位负担。并在同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通知,明确鼓励企业、机关、团体等兴办幼儿园和托儿所,企事业单位在当时还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儿童照料的工作。这一时期城镇的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具有明显的“去家庭化”取向,城市儿童照顾的主要形式由家庭照顾变成了机构照顾,从而对妇女就业和男女平等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正向影响。1969年后,生育保险成为了企业的直接责任;1988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将女职工的产假增加到90天,但生育保险的成本由企业自行负担。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需要自负盈亏,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企业市场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不相适应,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也因此受到损害。1994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我国才正式确立了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全国性政策,但由于缺少市场化的政策,使得托幼服务市场的“失灵”现象日趋严重,高品质的托幼资源极度稀缺,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降低了女性怀孕和分娩的压力,但是提升了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照顾儿童的要求,所以女性在这一阶段受到的生育惩罚相对于建国初期鼓励生育的时期,反而更加严重。近期,多胎政策的出台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育惩罚。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2019年相继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和《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两项政策,前者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 000元(每月1 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后者鼓励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两项政策明确表明了政府分担生育成本的决心,其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
目前关于生育惩罚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涉及到人力资本、补偿性差别、福利政策、工作投入、雇主歧视、个人选择与偏好等多个方面[61]。然而,上述解释各自独立,缺乏系统性,也没有刻画出各个理论间的联系。基于此,本章围绕生育与生产的矛盾,介绍家庭制约论、人力资本论和雇主歧视论,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
“母性”是当代成年女性的主要身份,强化了女性的性别特征[62]。早期的科学研究曾从进化论的角度断言“母性”是雌性生物“保护和改善后代的生存条件,以保证自身群体基因延续”的一种本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学家逐渐发现“母性”是在女性怀孕过程中产生的激素与长期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28],甚至主要是一种社会构建的标签[63]。在“母性”观念中,“密集性母职”占主导地位[64],它认为:母亲是养育后代的中心,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子女的需求高于母亲的个人需求,母亲需要持续不断地满足子女所有的需求;母亲照顾子女的劳动价值高于市场劳动。“母性”中的“母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女性在抚育后代中做出自我牺牲时的自豪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定。
家庭制约论认为生育惩罚主要源于女性投入在家庭中无酬劳动的时间和精力对其有酬劳动产生的牵制。“母职”是当代社会对女性身份期望的核心。女性长期以来被认为应当主要承担家庭无酬劳动。即使在美国及北欧等性别平等指数相对较高的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长也不及女性的一半[65]。而对于大部分育有子女的家庭,家庭无酬劳动中照料子女的责任更是由妻子承担[66]。虽然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男性相较于过去分担了更多的家庭无酬劳动[67],但整体而言,女性家庭无酬劳动的时间并没有显著减少。
时间可用性理论认为女性更擅长家务,基于整个家庭效用的最大化目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便产生了[19]。相对资源理论假设夫妻双方都不喜欢做家务,家务劳动分工是根据双方所占有的资源在婚姻生活中进行的议价表现,反应的是二者间的权力关系[68]。性别意识理论认为家务分配实质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符号性表现[69],女性更多时候的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社会主流认可的范式去实践黏着在性别符号上的责任,因此即便女性的收入高于男性,为了补偿不合规的性别角色,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反而增加[31]。结合时间可用性理论、相对资源理论和性别意识理论(我们把这3种解释都归入家庭制约论),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社会性别观念对“母职”的期望,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使得其投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精力减少。
一项针对男女成就动机的实验形象地刻画出了男女成就动机差异[70]。如图13所示,当成就动机的目标是有酬回报时,男性的成就动机高于女性;当成就动机的目标替换为子女直接受益品时,女性的成就动机显著增加。尽管一项针对香港中年已婚华人妇女的身份认同展开的田野调查显示,有77%的被访者表达出对职业女性的羡慕[29],但在事业上的成就动机和女性对于“母职”的身份认同感中做选择时,女性往往对于母亲的身份的认可要远比职业身份多[71]。即使那些强调个人追求和成就的女性个体而言,也依然保持着“照顾和养育后代的强烈责任感”,并以母亲的身份,通过发现个人对于他人而言的重要性,来完成对自我价值的肯定[72]。家庭制约论认为这是导致生育惩罚在个人观念上的根本原因。

图 13 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激励目标时选择是否参加竞争的比例[70]
-
人力资本论认为女性因为生育行为而产生的在工作时间上的中断或间歇,会引发其在职业选择及收入回报中受到的惩罚。时间上的中断会影响求职者工作经验的积累,造成其自身能力的不足。对于不同职业,由于学习成本的不同,中断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文献[5]将一个职位所需完成的工作拆分成多个任务并将其分类为抽象性任务、重复性任务和体力性任务三大类。分析显示,抽象性任务所占比重越大,该职位学习成本越高,需要的连续性投入也越大,生育引起的时间中断产生的惩罚也越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职位而言,虽然求职者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最后的收入回报呈正相关,但这种相关并非线性——兼职工作的回报要远远低于全职。文献[73]指出,相比于兼职律师,24小时在线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回报显然是高出一大截——从事全职工作平均工资率要高于兼职工作。
而女性,由于社会观念影响,承担了更多生产后的抚育任务。在生育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生理和育儿责任完全没有办法投入工作(工作时间中断,处于产假或离职状态),或者没有办法全力投入工作(工作时间间歇,处于兼职状态)。这一方面带来被动的生育惩罚——工作经验中断削弱了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在知识更新速度较快的行业尤甚,同时又因为无法投入具有足够竞争力的长时间工作精力,使得当前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也减少了后续职业晋升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会产生主动的生育惩罚——为了照顾好子女,女性更倾向选择对家庭更友好的职业和企业,如能提供更灵活的工作环境和时间的公共事业部门[4]。这类工作往往收入水平较低,晋升空间也较少[10]。女性若选择兼职工作,则其收入水平往往很低且几乎没有晋升的可能。
-
雇主歧视论主要基于经济学中的偏好理论。通常而言,可以将歧视分为“偏好性歧视”和“统计性歧视”,二者成因略有差异,但又相互影响[74]。偏好性歧视是一种由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而产生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的非理性行为。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期待更多的是成为一个好母亲,主张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对于职场妈妈和那些并不准备成为母亲的女性而言,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力市场会被认为是一种违背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49]。有研究指出,女性事业上的成功与在大众中的受欢迎度成负相关,而这种不受欢迎又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印象,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75-76]。统计性歧视是信息不充分情况下为了效率最大化的措施。当雇主在录用员工时,由于缺乏对个体的充分了解,会倾向用群体的水平评估个体,造成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会造成工作上的间断,并向企业转移生育成本,导致雇主对未来求职的女性,不论生育与否,都会存有顾虑。
由于偏好性歧视的存在,雇主在做决策时会产生偏差,同时女性也会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产生悲观估计[17-18],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统计性歧视,然后反过来强化了对群体的偏见,产生恶性循环。以上原因,导致已经生育的女性遭受生育惩罚,还未生育但处于适龄生育阶段的女性遭受超前生育惩罚,即便根本不准备生育的女性也会受到观念形态上的惩罚。
-
如图14,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在生育惩罚的形成机制中,家庭制约论和人力资本论从供给侧出发,强调生育事件本身占用的时间精力削弱了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雇主歧视论则从需求侧指出雇主由于对女性生育成本的考虑和其他刻板印象,会降低对女性员工的需求。生育惩罚形成的关键在于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因此,我们认为缓解生育惩罚的核心是通过家庭和社会的努力,平衡女性的家庭和工作。在供给侧,通过倡导性别平等的观念,打破社会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缓解家庭对工作的干预,赋能女性;在需求侧,提供家庭友好制度的同时创造机会,为女性提供更为平等的职业发展平台,减少工作对家庭干预产生的负反馈。
-
赋能女性的目标是让女性能够做出不局限于家庭的多样性选择。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女性依然可以选择全职在家或者以家庭为主导,但当女性做出以事业为主导的选择时,她所受到的阻力应该尽可能小。
首先要提倡性别平等的观念,促进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的共识。中国建国伊始,就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鼓励妇女走向工作岗位,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就业,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让性别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如图15所示,文献[77]对比了2000年和201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指出中国的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溯的趋势。由于性别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地位平等上的,因此所有阻碍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观念,都会削弱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其他权利。我们需要警惕这一性别观念的回溯现象,避免家庭再次成为女性的唯一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选择。

图 15 男女性别观念变化情况。纵坐标是受访男性和女性中认同“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两个观点的人数比例[15]。
其次要提升女性职业发展的自信心,激发女性职业发展的成就动机。女性普遍的自信心要弱于男性[70],且对于风险的规避心态要高于男性[78],在职业晋升评估中,女性会思考更多的负面结果,从而相对于男性更少主动追求这样的机会[79]。因此,在早期教育和职场培训中,要特别注意帮助女性提高自信心。进一步地,在工作中,要依据女性成就动机的机理,调整外部绩效管理机制,提供诸如与子女相关的福利,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等,从而提升女性的竞争意愿[70]。
最后,要引入多方分担女性家庭劳动的机制。由于当前社会中,女性普遍承担了绝大部分养育子女的责任,为女性分担这部分无酬劳动便成为了缓解女性家庭对工作干预的关键。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公共托幼机构,市场有偿的家务劳动替代品均是职业女性用以减少家务劳动时间的选择[31, 61]。因此,政府加大幼儿托幼福利体系的建设,就能有效分担女性部分生育成本。此外,应该探索相应的男性育儿假制度,引导丈夫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受到的生育惩罚。由于中国大家庭文化的特殊性,祖辈照看孙辈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可以鼓励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与长辈同住,降低年轻女性照料家庭的负担。当然,与长辈和谐相处本身也是很高的家庭要求,需要审慎评估,避免在孩子之外产生更大的家庭负担,反而得不偿失。
-
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了“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这一概念,呼吁企业和政府一起为父母们提供充足的带薪育儿假、带薪哺乳假、优质且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子女补贴。关于工作场所的“家庭友好型”制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执行实施,如产假,育儿假等,另一类是在国家政策规定以外,企业自主选择实施的行为,如给予带薪产假(高于基本工资)、允许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配备家庭理解支持型领导,办公室设置母婴休息室等。因为第一类措施带有强制力,并不能完全代表工作场所的家庭友好程度,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第二类举措。
工作场所的家庭友好程度对女性生育惩罚有着很大的影响,相比于休假,提供灵活性工作可以更好地平衡家庭和生活的[73]。例如,针对分娩前后及带有3岁以下幼童的女性,推行弹性工作制,允许在家办公等措施,一方面可以为需要抚育子女的雇员提供更为灵活的时间安排,减少由于工作对家庭干预而产生的负反馈;另一方面,还能减小由于单一化长产假带来的人力资本贬值等问题。实施上述灵活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用人单位能解决针对当前薪酬与工作时间的非线性关系,重新设计有针对性地绩效考核方法,使得弹性工作和兼职工作能够获得于同等总时间投入的全职工作相当或相近的收入,且依然拥有公平的晋升机会。
国外很多大型企业都在推行各类家庭友好计划,并每年由第三方机构评选认证。美国跨国科技企业IBM是一家典型的实行家庭友好计划的企业,支持弹性工作制,既可以压缩工作周,也可以兼职;提供员工家庭医疗计划,定期举办员工家庭亲子活动;企业内部设置育儿室、阅览室、医疗室及活动室。而在东亚区域的韩国女性家庭部,也在2007年提出并通过了“促进构建家庭友好社会的相关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具体化家庭友好型企业的认证制度。在中国,处于领头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也在逐步发挥相应的社会责任,包括设立带薪产假及陪产假,建设企业内部托幼中心、发放子女教育补贴等。与海外尤其是性别平等指数较高的一些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创造家庭友好环境”的意识。在中国鼓励企业创造家庭友好的工作场所,需要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设计相应的家庭友好制度,并且通过给予这些企业相应的奖励和优惠,减少将社会生育成本直接转移到企业中去。
进一步地,应该基于女性承担高于男性的生育成本这一现实,适当对女性从业者延长其晋升通道开放的有效时间。这一思路,在学术界已经开始实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例如,女性学者在评定重要的人才计划时(包括长江学者、杰青优青等计划),年龄截止时间往往比男性多2~3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研究工作的放缓甚至中断。产业界也应该为女性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晋升通道,减少因为生育而导致的职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
文献[80]发现,远程办公的措施与企业整体的资产收益率和股本收益率呈正相关。但文献[81]却指出在考虑管理水平的差异后,上述正相关消失。同时,文献[82]质疑远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了人均生产力,而这可能与工作专注程度的降低有关。尽管通过对员工平衡家庭责任的目标诉求进行激励管理,理论上能提升人均绩效水平,但事实层面企业家庭友好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或者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制度才能产生正面影响,目前还存在争议或缺乏深入研究分析。
-
生育惩罚的问题是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能解释相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的两性差异。在量化生育惩罚的过程中,宏观上从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微观上从女性工资率和总收入的变化,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都存在极大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个体及其所处环境的差异,影响了生育带来的无酬劳动总量,以及有酬劳动回报。不论是家庭制约论中的母性因素,人力资本论中的间断因素,还是雇主歧视论中的刻板印象,其核心都是社会对女性,以及女性对自身的期望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我们认为,减少生育带来的职场负面影响,其核心是尽力平衡女性的家庭与工作。通过在社会中倡导性别平等,在家庭中分担无酬劳动,在工作中营造家庭友好氛围,帮助女性打破刻板印象,积攒更多做选择的力量,最终缓解生育惩罚。
基于本文述及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我们提出四点具体的政策建议。1) 改变单纯长产假的模式,在给定产假总时长的前提下,允许女方将产假时长在夫妻间分配,逐渐引导夫妻双方习惯共修育儿假。通过这种措施,改变长产假背后潜在的对女性主要承担照顾家庭责任的强化,引导家庭内部共同承担育儿责任。2) 宣传和推广弹性工作制,允许和鼓励企业通过提供更长时间的弹性工作替代一部分产假时间。政府通过财税奖励、资质评定和品牌正面宣传等方式鼓励企业创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成为家庭友好型企业。3) 改变过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相关专项所得税减免,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就业,优先减免在职工作女性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在职母亲的个人所得税。4) 将托幼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大力发展托幼市场,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建设各类托幼机构,引入不同层次的托幼服务,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需求。
目前关于职场性别不平等,包括生育惩罚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这类研究在对象上尚不平衡,在方法上尚不成熟。前者表现为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研究和结论都源自于欧美国家,而针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非常少。后者表现为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定性框架或者少量样本上,缺少足够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因此可信的定量化成果较少。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基于海量的微观数据,利用更先进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工具,覆盖更广泛的地区[83],从而帮助探讨缓解生育惩罚的更切实可行的路径。最后,我们列出若干尚待研究的开放性问题,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1) 无酬劳动总量与妇女婚姻、生育及工作状态之间有没有交互关系?在以前的分析中,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夫妻双方、其他家庭成员、家政服务人员和社会托幼机构等对家庭无酬劳动的分担额度,而把整个家庭的无酬劳动总量视为一个固定值,或者只是随着子女人数发生变化。事实上,妇女婚姻、生育及工作状态本身就可能影响无酬劳动的总量。譬如,一个全职太太可能比职业母亲花更多时间、以更高频率打扫卫生。所以,无酬劳动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高价值的,哪些是必要性和价值度都较低的,需要细致的研究。通过小范围访谈和大规模问卷调查量化女性自身家庭和工作状态与整个家庭总的无酬劳动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建立更精准的关于生育惩罚的经济学模型。
2) 如何量化托幼市场对生育惩罚的影响?传统研究认为生育惩罚的核心是生育和生产的矛盾,生育率低的国家,女性相对就业率应该更高。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36个OECD成员国的女性相对就业率与生育率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律——既存在正、负相关性都很强的国家,也存在相关性很弱的国家,国家间的差异性很大。是否存在一个中间变量能够解释二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托幼资源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托幼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数据,可望量化分析托幼市场在育儿方面的支持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生育惩罚。
3) 产假到底怎么休才合适?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报道对产假制度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生友好”政策。产假的延长加重了女性育儿的负担,同时还阻碍了女性产后再就业的可能,极大加重了女性的生育惩罚。与此同时,放弃和单纯缩短产假又是对女性生理健康的一种漠视。休多长时间的产假,如何休产假,成为亟待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产假的长度,还包括各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例如产假期间工作的多倍薪资,选择性兼职,弹性办公制度,夫妻分享育儿假等等。针对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的企业,最佳的休产假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企业和员工都应该有更多样、更高适应度的产假选择机制。
4) 适龄未育女性受到的超前生育惩罚有多强,变化趋势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雇主默认适龄生育女性将有较大的概率会选择生育,而生育又将导致一系列人力资本贬值的现象,因而在招聘过程中将会对适龄未育的女性劳动力产生一种基于预测的统计性歧视,俗称为超前生育惩罚。我们认为在中国,随着多胎制度的推行,超前生育惩罚会愈演愈烈。我们应通过大量真实人力资源数据,定量揭示当前中国适龄未育(甚至包括适龄少胎)的女性受到超前生育惩罚的强度,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
5) 行业间和区域间的生育惩罚差异大吗?不同行业间往往由于学习成本的不同而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技术类的岗位,对知识迭代的要求较高,因而生育带来的工作中断的惩罚力度可能更重。不同区域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观念形态的不同,也可能带来不同强度的生育惩罚。但是这种差异具体有多大,是否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或者新兴行业生育惩罚更小,目前还没有广为认可的结论,需要从海量人力资源数据中得到统计上显著且可信的结果。
致谢:感谢杨子曦、郑晨、王晓彤、杨小寒、王岩、岳仲涛、刘权辉、张彦如、马梦伶、王传赞、侯宇、刘文龙在搜集资料和文章修改方面的帮助。
Motherhood Penalty in Career Development
-
摘要: 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也会加剧其他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其中,生育惩罚是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能解释相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的两性差异。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历时悠久,但一直缺乏系统化的梳理。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生育惩罚进行量化,探讨了个人、家庭和政策层面影响生育惩罚的主要因素,特别就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本文强调生育与生产的矛盾,将关于生育惩罚产生的机制梳理为家庭制约论、人力资本论和雇主歧视论三个方面,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侧,提出通过赋能女性和创造机会的方式平衡家庭和工作,最终减轻生育惩罚的方法。文末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就若干开放性议题进行了讨论。Abstract: The gender gap in labor marke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gender inequality. It will also enlarge gender differences in other fields. Among them, motherhood penalty refers to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birth event on women career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explain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gender gap within labor market. Although extensive studies have been accomplished, a comprehensive landscape of this domain has not yet been built. In this survey, the related progresses, including the quant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motherhood penalty in different times and regions are presented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rength of motherhood penalty from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are discussed, where the emphasis is put on Chinese situations. Concentrating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and labor, this survey summarizes the known explanations into three different yet related theories: family restriction theory,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employer discrimination theory. From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the labor market, we suggest two ways, namely empowering women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help women balance their family and working duties. Lastly, we propose political recommendations and outline a number of open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es.
-
Key words:
- career development /
- gender equality /
- motherhood penalty
-
图 3 各国在STEM学科中的女性占比与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的关系(纵坐标为全球整体性别平等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数值越大表示越平等;横坐标为各国在STEM学科中的女性占比。这两个参数整体上呈现出负相关[7])
图 4 不同行业中人工智能人才的占比,其中浅蓝色为男性占比,深蓝色为女性占比。以第一行“软件与IT服务”为例,该行业从业人口中男性具备人工智能能力占32.5%,而仅有7.4%是女性,存在显著差距[3]。
图 5 中国城乡两性年收入分布[15]
图 7 1970~1995年间,OECD21成员国平均生育率(TFR)与15~6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PR)的相关系数随年份的变化[20]
图 8 丹麦女性与男性在生育事件发生前后的收入变化。纵坐标为相对于生育事件发生前一年的收入水平;横坐标为时间(以生育时间发生为参照)[4]。
图 9 不同现代化水平下妻子平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妻子的相对收入之间的关系[31]
图 10 不同婚姻状态中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周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52]
图 11 延长产假前后奥地利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上述女性样本中的分娩时间均为1990.6.1~1990.7.31,虚线表示延长产假改革前,实线表示延长产假改革后[55])
图 12 OECD各国与生育相关的政策组合差异。(图中的点为OECD成员国,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代表着两国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政策模式的相似性,距离越近越相似,每个国家点的大小代表该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在坐标轴上的典型性。横坐标表示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在职父母提供福利支持的程度:坐标轴左端的国家,政府福利制度更关注低龄儿童(例如公共托幼机构等)能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在生育和生产中产生的矛盾;横坐标右端的国家,政府福利制度的财政支出大部分投入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对女性生育惩罚的影响有限。纵坐标代表着产假期/育儿假的慷慨程度,处于纵坐标上端的国家产假时间更长[60]。)
图 13 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激励目标时选择是否参加竞争的比例[70]
图 15 男女性别观念变化情况。纵坐标是受访男性和女性中认同“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两个观点的人数比例[15]。
-
[1] UNITED NATION. Gender equality: Why it matters [EB/OL]. (2016-10-15).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R].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4] KLEVEN H, LANDAIS C, SØGAARD J E.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9, 11(4): 181-209. doi: 10.1257/app.20180010 [5] ADDA J, DUSTMANN C, STEVENS K.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2): 293-337. doi: 10.1086/690952 [6]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299): 493-517. doi: 10.2307/2228949 [7] STOET G, GEARY D C. The gender-equality paradox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8, 29(4): 581-593. doi: 10.1177/0956797617741719 [8] WANG M T, ECCLES J S, KENNY S. Not lack of ability but more choice: Individu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oice of career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5): 770-775. doi: 10.1177/0956797612458937 [9] DONG X, AN X. Gender patterns and value of unpaid care work: Findings from China’s first large-scale time use survey[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5, 61(3): 540-560. doi: 10.1111/roiw.12119 [10] HEGEWISCH A, HARTMANN H.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A job half done[R]. Washington DC, USA: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2014. [11] BURKE R J, MAJOR D A. Gender in Organizations: Are men allies or adversaries to women s career advancement?[M].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12] BRUSH C, GREENE P, BALACHANDRA L, et al. Women entrepreneurs 2014: Bridging the gender gap in venture capital[R]. Babson Park, MA, USA: Babson College, 2014. [13] PANDE R, FORD D. Gender quotas and female leadership[R/OL]. (2011-04-07). https: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9120. [14] SHELTZER J M, SMITH J C. 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 sciences employ fewer wome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28): 10107-10112. doi: 10.1073/pnas.1403334111 [15]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12):28-31. The Third Survey Group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The main data report of the third survey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1(12): 28-31. [16] BERTRAND M, GOLDIN C, KATZ L F.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3): 228-55. doi: 10.1257/app.2.3.228 [17] YANG X, GAO J, LIU J H, et al. Height conditions salary expectations: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data in China[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8, 501: 86-97. doi: 10.1016/j.physa.2018.02.151 [18] 王军, 高见, 杨枭, 等. 在线数据揭示预期薪金的影响因素[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19, 48(2):307-314. WANG Jun, GAO Jian, YANG Xiao, et al. Online data reveals factors affecting expected salary[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19, 48(2): 307-314. [19] BECKER G S,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Boston,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 AHN N, MIRA P. A note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ra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 15(4): 667-682. doi: 10.1007/s001480100078 [21] KÖGEL T. Di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within OECD countries really change its sig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 17(1): 45-65. doi: 10.1007/s00148-003-0180-z [22] 山口一男. 关于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真实关系: OECD各国的分析[R]. 东京, 日本: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2005. SHAN Kou-yi-n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ertility rate: An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R]. Tokyo, Janpan: The Research Institu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RIETI), 2005. [23] LUCIFORA C, MEURS D, VILLAR E. Children, earnings and careers in an internal labor market[EB/OL]. (2017-08-31). http://www.aiel.it/cms/cms--files/submission/all20170831111248.pdf. [24] GANGL M, ZIEFLE A. Motherhood, labor force behavior, and women’s career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in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J]. Demography, 2009, 46(2): 341-369. doi: 10.1353/dem.0.0056 [25] PETERSEN T, PENNER A M, HØGSNES G. The within-job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Norway, 1979−1996[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0, 72(5): 1274-1288. doi: 10.1111/j.1741-3737.2010.00764.x [26] 於嘉, 谢宇. 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14, 38(1):18-29. YU Jia, XIE Yu.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women's wages in China[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4, 38(1): 18-29. [27] HRDY S B. 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246-248. [28] HO P S. Eternal mothers or flexible housewives? Middle-aged Chinese married women in Hong Kong[J]. Sex Roles, 2007, 57(3-4): 249-265. doi: 10.1007/s11199-007-9255-8 [29] LAI A C, ZHANG Z X, WANG W Z. Maternal child-rearing practices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Chinese families: A comparative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0, 35(1): 60-66. doi: 10.1080/002075900399529 [30] JIA N, DONG X Y.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urban China: Investigation using panel data[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37(4): 819-843. [31] 於嘉. 性别观念, 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 社会, 2014, 34(2):166-192. YU Jia. Gender ideology, modernization, and women’s housework time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4, 34(2): 166-192. [32] TODD E 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family gaps in women's wages: Evidence from fiv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R/OL]. (2001−01−25). http://www.lisdatacenter.org/wps/liswps/246.pdf. [33] AMUEDO-DORANTES C, KIMMEL J. The motherhood wage gap for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and fertility delay[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05, 3(1): 17-48. doi: 10.1007/s11150-004-0978-9 [34] TANIGUCHI H. The timing of childbearing and women's wag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9: 1008-1019. [35] COVERMAN S.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85, 26(1): 81-97. doi: 10.1111/j.1533-8525.1985.tb00217.x [36] WILDE E T, BATCHELDER L, ELLWOOD D T. The mommy track divides: The impact of childbearing on wages of women of differing skill levels[R]. Cambridge, MA,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37] CAUCUTT E M, GUNER N, KNOWLES J. Why do women wait? Matching,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incentives for fertility delay[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2, 5(4): 815-855. doi: 10.1006/redy.2002.0190 [38] ANDERSON D J, BINDER M, KRAUSE K.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revisited: Experience, heterogeneity, work effort, and work-schedule flexibility[J]. ILR Review, 2003, 56(2): 273-294. doi: 10.1177/001979390305600204 [39] LOUGHRAN D S, ZISSIMOPOULOS J M. Why wait? The effect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on the wages of men and women[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9, 44(2): 326-349. doi: 10.1353/jhr.2009.0032 [40] BAXTER J. Domestic labour and income inequality[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992, 6(2): 229-249. doi: 10.1177/095001709262004 [41] JOHNSTON D D, SWANSON D H. Constructing the “good mother”: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ing ideologies by work status[J]. Sex Roles, 2006, 54(7-8): 509-519. doi: 10.1007/s11199-006-9021-3 [42] SMITH R S.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and public policy: A review[J]. ILR Review, 1979, 32(3): 339-352. doi: 10.1177/001979397903200304 [43] FILER R K.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J]. ILR Review, 1985, 38(3): 426-437. doi: 10.1177/001979398503800309 [44] WALDFOGEL J.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women’s wag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2): 209-217. [45] GLASS J, CAMARIGG V. Gender, parenthood, and job-family compatibi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 131-151. doi: 10.1086/229971 [46] GLASS J.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on working conditions[J]. Social Forces, 1990, 68(3): 779-796. doi: 10.2307/2579353 [47] MILLER A R. The effects of motherhood timing on career path[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1, 24(3): 1071-1100. doi: 10.1007/s00148-009-0296-x [48] CHERLIN A J.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nonmarital childbearing[J]. Out of Wedlock: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marital Fertility, 2001(1): 390-402. [49] ASHBURN-NARDO L. Parenthood as a moral imperative? Moral outrage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voluntarily childfree women and men[J]. Sex Roles, 2017, 76(5-6): 393-401. doi: 10.1007/s11199-016-0606-1 [50] BUDIG M J, ENGLAND P.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2): 204-225. doi: 10.2307/2657415 [51] JACOBS J A, GERSON K. The endless day or the flexible office? Working hour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gender equity in the modern workplace[R]. Philadelphia: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1997. [52] SOUTH S J, SPITZE G. Housework in marital and nonmarital househo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59(3): 327-347. doi: 10.2307/2095937 [53] LALIVE R, ZWEIMÜLLER J. How does Parental leave affect fertility and return to work? Evidence from two natural experime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363-1402. doi: 10.1162/qjec.2009.124.3.1363 [54] GANGL M, ZIEFLE A. The making of a good woman: Extended parental leave entitlements and mothers’ work commitment in Germa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5, 121(2): 511-563. doi: 10.1086/682419 [55] GAUTHIER A H.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7, 26(3): 323-346. [56] HAAN P, WROHLICH K. Can child care policy encourag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model[J]. Labour Economics, 2011, 18(4): 498-512. doi: 10.1016/j.labeco.2010.12.008 [57] BLANK R M. Evaluat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4): 1105-1166. doi: 10.1257/.40.4.1105 [58] AZMAT G, GONZÁLEZ L. Targeting fertility and female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income tax[J]. Labour Economics, 2010, 17(3): 487-502. doi: 10.1016/j.labeco.2009.09.006 [59] DIPRETE T A, MORGAN S P, ENGELHARDT H, et al.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 22(5-6): 439-477. [60] THÉVENON O.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37(1): 57-87. doi: 10.1111/j.1728-4457.2011.00390.x [61] 李芬, 风笑天. “对母亲的收入惩罚” 现象: 理论归因与实证检验[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3):74-83. LI Fen, FENG Xiao-tian. "Punishment on Mother’s Income" phenomenon: Theoretical Attribution and Empirical Test[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16(3): 74-83. [62] MCMAHON M. Engendering motherhood: Identity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women’s lives[M]. New York, USA: Guilford Press, 1995. [63] CHODOROW N J. Gender,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in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M]//ZANARDI C. Essential Papers on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New York, US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64] HAYS 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M]. City of New Haven,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5] BIANCHI S M, MILKIE M A, SAYER L C, et al.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Social Forces, 2000, 79(1): 191-228. doi: 10.2307/2675569 [66] 张航空. 儿童照料的延续和嬗变与我国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J]. 学前教育研究, 2016(9):14-22. ZHANG Hang-kong. The continu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ld ca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ld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children aged 0~3 years in China[J].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16(9): 14-22. [67] HOOK J L.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2003[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71(4): 639-660. doi: 10.1177/000312240607100406 [68] MCELROY M B, HORNEY M J. 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s: 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1, 22(2): 333-349. doi: 10.2307/2526280 [69] GREENSTEIN T N.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58(3): 585-595. [70] CASSAR A, WORDOFA F, ZHANG Y J. Competing for the benefit of offspring eliminates the gender gap in competitivenes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113(19): 5201-5205. doi: 10.1073/pnas.1520235113 [71] NORTON T R, GUPTA A, STEPHENS M A P, et al. Stress, rewards, and change in the centrality of women’s family and work roles: Mastery as a mediator[J]. Sex Roles, 2005, 52(5-6): 325-335. doi: 10.1007/s11199-005-2676-3 [72] ODONNELL L N. The unheralded majority: Contemporary women as mothers[M].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 1985. [73] GOLDIN C.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4): 1091-1119. doi: 10.1257/aer.104.4.1091 [74] BECKER G S.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M]. Chicago,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75] PARKS-STAMM E J, HEILMAN M E, HEARNS K A. Motivated to penalize: Women’s strategic rejection of successful women[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8, 34(2): 237-247. doi: 10.1177/0146167207310027 [76] HEILMAN M E, WALLEN A S, FUCHS D, et al. Penalties for success: Reactions to women who succeed at male gender-typed task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3): 416. doi: 10.1037/0021-9010.89.3.416 [77] 许琪.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 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 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3):33-43. doi: 10.3969/j.issn.1004-2563.2016.03.004 XU Qi. Trend, source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change of gender-role attitud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wo indicator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6(3): 33-43. doi: 10.3969/j.issn.1004-2563.2016.03.004 [78] ECKEL C C, GROSSMAN P J. Men, women and risk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J].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2008, 1: 1061-1073. doi: 10.1016/S1574-0722(07)00113-8 [79] GINO F, WILMUTH C A, BROOKS A W. Compared to men, women view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s equally attainable, but less desirabl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40): 12354-12359. doi: 10.1073/pnas.1502567112 [80] SANDS J, HARPER T. Family-friendly benefit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Business Renaissance Quarterly, 2007, 2(1): 107-126. [81] BLOOM N, KRETSCHMER T, VAN REENEN J. Are family-friendly workplace practices a valuable firm resour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2(4): 343-367. doi: 10.1002/smj.879 [82] LEE S Y, HONG J H. Does family-friendly policy matter? Testing its impact on turnover and performan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1, 71(6): 870-879. doi: 10.1111/j.1540-6210.2011.02416.x [83] GAO J, ZHANG Y C, ZHOU T. Computational socioeconomics[J]. Physics Reports, 2019, 817: 1-104. doi: 10.1016/j.physrep.2019.05.0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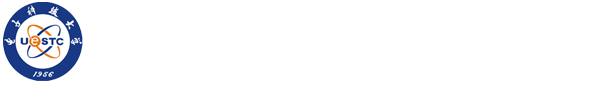
 ISSN
ISS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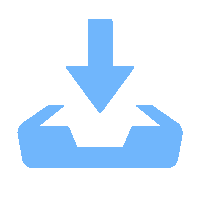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